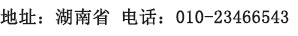作者:朱德瑛阳光穿过御寒的塑料布倾撒在水泥地上面,让有点昏暗的屋子稍稍通亮了一些。电视机里播放着冗长的家庭连续剧,她的身上穿着一件许多年前的暗蓝色毛衣,带着老花镜伸张着脖子,坐在距离电视不到半米的椅子上,时不时摘下花镜凑到嘴巴前哈一哈气,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手绢擦拭下镜片再重新戴上,努力想把画面看得更清晰。电视剧里上演的某些情节她或许并不在意,大抵只是想给自己找一些事情做,哪怕只是听一听从电视机里发出的点点声响,好像透过这个小小的老旧电视机,她就能感受到些许来自这个世界的喧嚣和热闹一样…这个人便是我的姥姥。“十二岁成为童养媳,这才有了我自己的名字。”姥姥的名字叫鲁金平,在十二岁之前,她一直没有名字,家里的长辈们都称她作“军妮儿”,因为那时候的人们常说:没名字的闺女儿好养活。我问她后来怎么又取了“鲁金平”这个名字,姥姥说因为她婶婶当时要把十二岁的她送到邻家去做童养媳,家里人怕别人笑话她没名字,所以才临时随便取了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姥姥并不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是在18岁时随太姥爷从山东省东平县人口迁徙才因缘际会来到牡丹江市林口县源发村,这一待就是一辈子,她的青春与苍老、所有美好和不美好的记忆都留在了这里……姥姥是家里的大姐,她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那个年代,整个鲁姓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加起来有近二十几口人。家里本是做杂货买卖生意,存了一些收入,可后来在分家后太姥爷被划为了贫农,积蓄跟他也没了多少关系。在姥姥八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因病去世,由于没有太多的土地,太姥爷决定带着姐弟三人去东北流浪,但当时姥姥的爷爷奶奶都不同意,太姥爷拗不过他们,一气之下自己跑到哈尔滨闯荡,将姥姥姐弟三人留在了叔叔家。即便有着血缘关系,可在叔叔家的日子,用姥姥的话就是:“有爹有妈有人经管,没爹没娘受人欺负。”姥姥的妹妹被送到没有子女的远方亲戚家里寄养,她和弟弟在叔叔家帮衬着做一些杂务。叔叔家的孩子到了年纪可以去学堂上学,但姥姥姐弟两个一早就没有了读书的机会。每天早晨姥姥都要早起帮着婶婶做饭、刷碗,有时候粮食不足,她还要去田地里捡些地瓜叶或剩玉米回来做粥。在三四月份榆树钱儿长得最为繁盛的时候,姥姥要撸上两大缸,用水焯干,参上豆饼用锅蒸成菜团,够一家人吃上一阵子。那时候很少有热水用,虽然天气不那么寒冷,但是两大缸的分量也足以让她手裂出血。她和弟弟晚上睡的床是一个硬木板,上面铺着一层厚豆子皮,半夜冷得直打哆嗦,姥姥的弟弟好几次冻得尿了裤子。小时候不懂事,姥姥也会和叔叔的儿女们打架,不管是谁的过错,叔叔总会用绳子抽她,姥姥也有过年少脾气,一个小娃娃竟可以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徒步十八里地,但没了吃喝最后她不得不又返回去。懵懂无知,过了三年。十二岁的时候,婶婶为了节省家里的伙食,就想让姥姥到隔壁村去做童养媳,姥姥自己没有主意,只能任人安排。天刚亮,姥姥的姑姑就来到婶婶家,把姥姥带去了隔壁村,至此,“鲁金平”终于离开了这个不知道算不算是家的地方,再也没有回去过。“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这是姥姥被带到王家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她说她至今还记得那个男孩子的名字,叫王翔,要比自己小一岁。小子看起来老实敦厚,之后相处的日子也待姥姥很好,很多时候都是姥姥欺负他。在王家,姥姥还是做一些做饭烧火的杂活。当时年纪小,两个人并未发生什么。太姥爷一走就没了音讯,一直到八年后,他从东北回到了山东。听说自己的三个孩子都被送走,开始想把他们一一接回身边。当时王家并不是很情愿,太姥爷找了村里支书说情,王家老太太比较仁义,这才说:“人你领走吧,我们家王小儿可以等到十八岁。如果还能送回来的话,我们就还是一家人。”“多个人多双筷子,这句话让我16年坐了11年的月子。”将孩子陆续接回身边后,太姥爷就报名了迁民名额,历经5天的火车,他们一行人来到了黑龙江这片土地上。那时候的农村是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耕种,记工分,得口粮。原本以为来到了新的环境,有了草房,有了柴火,有了自食其力的机会,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可刚到东北不久,太姥爷就生了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姥姥认识了我的姥爷。介绍人也是从山东迁民过来,是姥爷的远方亲属。正是因为有着老乡情节,来往比较密切,所以他偶尔也会给姥姥家送去一些吃食。没过多久,太姥爷便去世了,离世之前他将姥姥姐弟三个一并都交托给姥爷。在太姥爷去世的第六天,姥姥就被他接回了家里。五个月后,十八岁的姥姥嫁给了二十五岁的姥爷。两个人在屋里拜了天地,在厨房拜了灶王爷,就算是有了仪式开始搭伙过日子,这两个人一辈子也没有一张结婚证。婚后,姥姥除了日常去生产队干活之外,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生孩子。在姥爷的固有思想里,人口就是财富,生得越多,名声越好,多个人只是多双筷子。也是这句话,让姥姥在之后十六年的时间里,坐了十一年的月子……在二十岁的时候姥姥生了大姨,然后又接连生了五个闺女,其中有两个没有存活下来。因为重男轻女的守旧观念,姥爷一直埋怨她不生儿子,对外说她没用。后来终于生了两个儿子,姥姥便说不想再生,但姥爷说之前能生六个闺女,那就可以再生六个小子。没成想,后面又连续添了两个女娃娃,也就是我妈和我小姨。姥爷这才作罢,在生孩子这条路上放过了我姥姥。其实,姥姥的婆婆对她也很不好,在她怀孕的时候,从来也没有伺候过月子,也没有帮忙照顾过孩子,甚至在生气的时候还经常骂姥姥是个外人。姥爷身上“勤劳”的标签从年轻一直伴随到现在,一提到“孙树发”这个名字,村里人的反应都是能吃苦能干活。除了在生产队种地之外,姥爷和姥姥还开过豆腐坊卖豆腐,养了近二十年的老母猪,一点点攒下家底,供孩子上学,但几个孩子上到小学毕业就都不想继续念下去。两个人的分工很明确,姥爷在外赚钱,姥姥在家边哄孩子边干活。在生完大舅满月后的第三天,正值春寒,她一口气挑了十五担水浇灌白菜,只为了能在端午节之前长好拿出去卖掉换钱。在生完小姨的第十二天,外面刮着大风,草房上的草被吹落下来,姥姥骨缝还没长好,就一个人拿着梯子爬上屋顶压房草,姥姥说,那天的大风她一辈子都能记住,好像真的吹进了骨头里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两个人吵架拌嘴是家常便饭,姥爷有理无理都是绝对权威,但是姥姥对姥爷的脾气也并不是逆来顺受,她也有自己的倔强,也会反抗,也曾离家出走过,但是还没走出村,就被这一个接一个的孩子哭闹着拉扯回来,其实她自己心里清楚,除了这里,她也没什么地方能去了……“我没有遗憾,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我就是这种命。”从小到大,姥姥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坚强,她这一生在鬼门关走了好多个来回。除了生孩子之外,在四十九岁的时候,她跟着姥爷一起去田地里干活,回来的路上牛车抛锚,姥姥当时被甩出很远,不省人事,医院经过六个小时救助才缓了过来,连续吃了两年药才彻底治好。在这两年时间里,有一次在路上摔倒,伤得尤其严重,一直站不起来,家里人都十分担心,还好最后姥姥又撑了下来。在五十一岁的时候她得了糖尿病,之后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姥姥今年七十九岁,姥爷八十六岁,年近九十岁的老头依然闲不下来,在村里的北山开垦新地、种树、养牛,姥姥虽然走路缓慢,但每天依然为姥爷热好饭菜。她说:“我和你姥爷一共生了八个孩子,但是从来也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感觉,我们俩都是相互习惯了。”前年,舅舅在镇里建了一座养老院,一直想接两个人过去,但姥爷始终不情愿,儿女们都劝说姥姥身体不好,早点过去可以享享清福,但姥姥见姥爷不肯去,她也犹豫着,想到如果自己去了的话,剩下姥爷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即便没有爱过,但也还是惦念着,两个人就这样继续在吵闹和踏实中生活着。记得当时看张艾嘉导演的《相爱相亲》,被里面姥姥的执念所感动,她用一生的时间将思念寄托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上面,没有埋怨,也没有孤独,不管是生是死,她只想把丈夫留在身边,最后说出口的一句“我不要你了”,怕是已经用了毕生的勇气。在我看来,姥姥和电影里的姥姥很像,虽然她和姥爷两个人之间没有很深入的感情,但是内心深处还是有着对固有爱情的坚守,这个执念圈住了姥姥一辈子。我问姥姥:“这一生还有有什么遗憾吗?”她说:“我和你姥爷一辈子性格合不上,但是也凑合过了一辈子,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我就是这种命……”对幸福和不幸福的定义,姥姥仿佛始终也没有明确过。其实我知道,对她来说,活着已经是生活的全部意义了。人间本就倾斜摇晃,希望我们内心深处总会有一处信仰能够带给光亮。